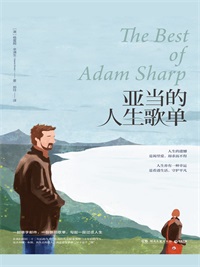《亚当的人生歌单》 第一章 免费试读
旧日恋人的邮件
我回到诺里奇的家中,开始研究皮特·贝斯特。贝斯特是披头士乐队的第一任鼓手,但没有多少人还记得这个名字。突然,一封电子邮件从屏幕下方跳了出来。
发件人:angelina.browntpg.com.au
嘿。
就一个字。嘿。在我们相识二十二年后的今天,在我们失去联系整整二十年后的今天,安杰利娜·布朗,我失去的爱人,决定改变世界,写下这个“嘿”。
该有首歌记录下这个时刻。赫尔曼的隐士们乐队发行于1969年的热门单曲《我多愁善感的朋友》[1]透过耳机的介质,在我的颅骨内回响起来。这一刻,我的人生唱机音乐剧里给这首歌留出了位置,里面的每句歌词唱的都是那个女孩,她是怎么让他的心碎成了两半。这不是什么出自语言大师的伟大作品,但足以引起共鸣。看着消息弹窗,我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个发件人。
这是不是她第一次想起我?是不是她的思绪飘回到《宛如祈祷者》[2]还占据着公告牌首位的年代,她想知道那个和她在墨尔本一家酒吧里相识相爱的男人过得好不好,或者她只是在翻看联系人列表,心血来潮想要知道他正在干吗?
点击亚当·夏普,敲上几个字母,发送。
不止于此。首先,我肯定不在她的联系人列表里面。自打电子邮件发明以来,我们从未联系过。
另外,她的电邮地址显示她还在澳大利亚。我查了查世界时钟:诺里奇时间下午1点15分对应墨尔本时间0点15分。她喝多了吗?她离开查理了吗,还是查理离开了她?也许他们五年前就分开了。
她还在用着自己的娘家姓。这也算不得惊喜,毕竟她之前也没有冠夫姓。
我几乎对查理没什么了解——连他姓什么都不知道。我的头脑里默认他和她有着一样的姓氏。查理·布朗,漫画里那个戴着棒球手套的秃头小孩:是个高飞球,查理·布朗。别脱手,查理·布朗。然而在现实世界,我才是那个让球脱手的家伙。
一天晚上,几杯啤酒下肚之后,我开始在谷歌上搜她的名字,没什么进展。和安杰利娜同名的有一位致力于推动男女机会平等的干事,还有一位在报纸上写专栏的作家。想象她投身诉讼领域,或是发表洞见,都让我浸满了啤酒的大脑有点招架不来。除非我用上图片搜索,但我决定停下来。安杰利娜曾经是——过去一直都是——让我上瘾的名字,想要摆脱这种瘾,唯一的办法就是完全戒断。
或许是吧。时间过去了这么久。就好像每个酒鬼都想要证明自己的酒精依赖症已经治愈了一样。毫无疑问,在经历了二十年坚贞的婚姻关系之后,我完全可以和过去的恋人发上一两封邮件。毕竟,用美国人的说法,是她先向我伸出了手。
或许她命不久矣,想要把过去的事情理理清楚。产生这样的念头完全要归咎于早餐时和母亲的对话。或许她和查理只是想来英格兰北部度个假,提前向我咨询:“如何在一个又冷又糟糕的地方规划假期,可以躲开没完没了的大晴天?”如果我连这种无伤大雅的询问都不能安心回复,那我该怎么定义和克莱尔的关系呢?
一直到晚上,我都还没有回复安杰利娜的邮件,还在权衡各种选择。克莱尔回了家,我们两人大呼小叫的对话声从我的房间传出去,直到楼梯下面。我可以想象到她的样子:穿着只有参加重要会议时才会穿上的灰色西服套装,搭配绿色围巾、粗跟靴子,整个人被垫到足有五英尺四英寸高。
“对不起,会议有点超时。晚饭闻起来很不错。”
“杰米·奥利弗的菜谱。鸡肉砂锅。我吃完了。”
“想来杯酒吗?”
“当然——已经开好了一瓶,在冰箱里。”
“你妈妈怎么样?”
“结果还没出来,她有点被吓到了。”
“代我向她问好了吗?”
“忘了。”
“亚当……下次你最好记住。喂埃尔维斯了吗?”
“要是没喂,你应该能看出来。”
这就是我们之间关系的写照,安杰利娜的邮件可能会是对我们的考验。我们是关系良好的一家人。我们不吵架,周末一起吃饭,互相照顾,是好朋友。不会有人为这种事情写首歌,但能说的其实有很多。我们的情况至少要好过我在参加酒吧小测时的队友希拉和她的丈夫查德。这两个人可以把很多人都照顾得很好,唯独不懂要怎么互相照顾。还有我们的朋友兰德尔和曼迪,他们两人依靠试管技术生了一对双胞胎,眼下正因为双胞胎的监护权打得不可开交,战场一路从圣何塞蔓延至利物浦。还有我的父母,也是一对不错的反面教材。
但在过去几年,我们之间的浪漫感觉几乎消耗殆尽。两个月前,我在书房里添了一张单人床。从表面上看,是我睡觉打呼的毛病影响了克莱尔的睡眠。她最近忙于软件公司的收购洽谈,需要充分的睡眠。我们的夫妻生活也随着我搬离卧室而结束了,我以为自己会怀念它,但实际上似乎并没那么想。我不知道这是好是坏。
我们的情况可能和许多同龄的夫妻没什么分别。如果把我们之间的问题都一股脑推给一段二十二年前就结束了的恋情,未免显得有点过分。在专注于解决数据库调试的问题,努力回想起疯狂老狗嘟哒乐队[3]主唱的名字,或是在克莱尔上班前在她额头印上一吻的时候,我从未想起过安杰利娜。只有在听音乐的时候,或是偶尔在钢琴上弹起一首歌的时候,安杰利娜这个名字才会在我的头脑中闪过。只有在那短短的几分钟,或是几小时,我才会回想起1989年。
我在一家酒吧演奏——不是小酒馆,而是一家酒吧——在墨尔本,位于中心城区近郊的菲茨罗伊,沿着维多利亚大道上的一段楼梯上去。在那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处地方会营业到很晚,这儿就是其中一处。顾客大都是雅皮士和婴儿潮一代。在那个时候,婴儿潮一代意味着出生于战后不久的一群人,而不是像我这样,看起来比他们晚生了二十年的家伙。
大部分时候,婴儿潮一代要多过雅皮士,这让我对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曲子得以充分练习。傍晚时分,人流十分平稳。不少人会在晚饭后过来,让酒吧变得热闹起来。还有从其他小酒馆过来的酒客,手里甩着雨伞,把厚大衣和羊毛帽子堆在凳子上,点上一杯冰凉的拉格啤酒。已经7月初了,冬天过半,但阳光尚未如约来到澳大利亚。
酒吧的内部装潢肯定达不到获奖的级别,不过是一家小酒吧,里面摆着八到十把椅子、十几张小桌子、一对皮质沙发,墙上贴着老电影的海报。没有餐食供应——只有些酒吧小吃。客人一旦多起来,站着的人就要多过有座位的人,闹哄哄的环境和香烟气反倒给酒吧加了不少分。
我在澳大利亚待了三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需要配置全新的数据库,我接下了这个持续十五个月的咨询项目,因此有机会走访该公司在全球各地的分支。我二十六岁,从计算机专业毕业不过五年,在新兴的科技浪潮中如鱼得水,那些三十多岁的老前辈就没那么幸运了。计算机是我的通行证,把我一路带离中低阶层和公立学校出身——在我抛弃了似乎水到渠成的摇滚梦之后。
在墨尔本的第一周,我和几个同事一起去了这家酒吧,庆祝其中一位同事当了爸爸,最后还在钢琴上弹了几首曲子。我记得我弹了《走吧,勒妮》[4]送给那个同样叫作勒妮的新生儿。酒吧店主是个糙汉子,名叫山克西,他给了我半品脱——他们叫一“壶”——拉格啤酒。我感谢他同意让我弹琴,他却说:“什么时候来弹都行,朋友。”
我接受了他的邀请,酒吧也成了我展开社交生活的场所。山克西给我提供酒水,我在钢琴上放了个罐子收小费。在酒吧的日子过得不错,但绝不是因为收入多有吸引力。我的日常工作薪水可观,还有一份食宿补贴,支付公寓式酒店的费用。酒店位于布朗斯威克街,在一家素食餐厅楼上,距离办公室搭电车只要十五分钟,距离酒吧步行只需十分钟。
对于这架钢琴,我已是了如指掌:琴是本地生产的,比尔牌,很旧,但音色不错,配有一个麦克风和一个小小的扩音器。有时,我还会在上班路上或是晨跑之后,突然出现在酒吧,为清洁工人弹上一曲。
到了晚上,事情就不一样了。如果没有这架琴,我可能只是个孤独的酒客,自己支付酒钱,找不到任何理由和其他人说话,也不会有人主动和我搭话。我就会有大把时间沉溺在生活的空洞里面。
我没有看见她走进来。她向钢琴走来的路上,我才注意到她。在这个全城人都喜着黑衫的地方,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羊毛连衣裙、一对高筒靴。二十几岁,齐肩的深棕色长发映衬着雪白的肌肤,加上鞋跟有五英尺七英寸高。
她的手里拿着一杯粉色的鸡尾酒。严格说起来,我们这里是一家鸡尾酒吧,但这儿毕竟是澳大利亚,大多数人还是喜欢喝啤酒、红酒,还有简单的混合饮品,除非他们想来点“一口闷”——像是B52和烈焰兰博基尼这样的烈性酒。吧台后面的酒架更像是充充门面,山克西对鸡尾酒的了解也很有限。但今晚,他却调出了杯粉色的东西,还加了樱桃和一把小伞。
我正在演奏范·莫里森[5]的《棕色眼睛的女孩》[6]。她站在钢琴一侧,离我那么近,让我无法不注意到她的存在,啜饮着鸡尾酒的女孩。
一曲终了,她鼓鼓掌,走上前,问道:“你会弹《因为这一夜》[7]吗?”
我有机会在更近的距离望着她,她的眼睛击中了我:大大的棕色眼睛,右眼下方一小条睫毛膏的印子挂在脸颊上。
我一般不会注意到香水味,除非是刚刚喷上的时候。也许她是刚刚喷了香水吧,香味是那么浓重而特别。补充一句,那是卡文克莱品牌的“迷恋”。自此以后,我在二十步开外就能分辨出这种香味。一位女士走上公交车,我偶然闻到同样的香气,所有的记忆便会一拥而上。好像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蛋糕[8]。
“帕蒂·史密斯[9]的歌。”她说,我还在思考是不是该告诉她睫毛膏的事。
“还有布鲁斯·斯普林斯汀。”
“再说一遍。”她大笑。
“布鲁斯·斯普林斯汀。他们两人一起写的歌。斯普林斯汀从未录制过录音室版本,但在现场专辑里收录过这首歌。”
“竹(珠)联璧合,是吧?真克(可)爱。”
她在模仿我的口音,但听起来更像是来自格拉斯哥,而不是曼彻斯特,配合那足以点亮整间屋子的迷人微笑。
我看了她一眼,假装受到了冒犯。
“对不起,”她说,“我不该这么无礼。我只是很喜欢你的口音。”
我决定冒上无礼的风险,伸出手指划过左侧脸颊。
我们各自摸了摸脸颊,点点头,笑了起来。她明白我的意思了,蘸湿手指,却错误地揉到了另一侧。后来,她换了边,右脸颊上的印子很快糊成了一团。
“等一下。”我说着,向吧台走去,那里放着一沓纸巾。回来的路上,我发现酒吧里安静下来,不仅是因为钢琴手停止了演奏。每个人——不管是吧台后面的山克西,还是门口穿着大衣的那对夫妻——都在看着我,看着我们。我不想在大庭广众下演奏,尤其在这种敏感的时刻,我不想让自己注意到她刚刚可能在哭。
我用纸巾擤了擤鼻子,塞进口袋,坐回到琴凳上。
“《因为这一夜》,是吧?”
她用手背蹭了蹭脸,环顾四周。
“没问题,”我说,“基本都会弹。”
“你介意我唱上一段吗?”
通常来说,面对“能否与乐队合唱”这样的问题,答案都是礼貌地说句“不能”,这样的答案是经验使然,同样也是来自我父亲的忠告。他曾经——据他自己说——有一条严苛的规定,无论他在哪一个乐队,任何人,任何人都不能和乐队合唱或是合奏。
“如果埃里克·克莱普顿[10]进来想要弹上一曲,我会直接让他滚蛋。如果管事的喜欢克莱普顿多过我们,那就让他来演吧,但我们绝不承担任何经济损失。”
他在就业保障方面传授过太多次经验,因此即便克莱普顿先生在曼彻斯特欣赏王首乐队的演出并接受经济回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个故事还是像真实发生过一样成了家族历史的一部分。
“你也知道,”我的妈妈总会说,“你爸爸曾经让埃里克·克莱普顿滚蛋——原谅我用词不雅,但他原话就是这么说的——所以他才能继续以此为生。这就是宝贵的经验。”
我爸爸到底有没有让吉他之神“滚蛋”我不清楚,但我相信面对同样年轻,有着大大的棕色眼睛的女士,他的反应一定和我一样,哪怕他的身上没有酒吧所有客人带来的压力——他们都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有事情发生。
“什么调?”
她唱得不错,所有人都爱她。我是说,人们都爱上了她。她的音准很好,倾注了全部感情,但她更像是奥莉维亚·纽顿-约翰[11],而不是黛比·哈利[12]或帕蒂·史密斯。
我又有什么资格去评价呢?她得到了全场观众的喝彩,大家都在要求她多唱一曲。短短五分钟的表演,她就征服了整个场地,我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想再唱点别的吗?”我问。
“《白日梦信徒》[13]?”她笑了,“他跟你口音一样,对吧,戴维·琼斯[14]?”
她的听力不错,对于过去的流行音乐也很熟悉。
“这次号码是多少,吉姆?”我模仿着戴维·琼斯。
她再次微笑起来:“七A。”非常熟悉。
“你会弹《一体两面》[15]吗?”她问。
“从来没听过。”
我弹起前奏。这不是什么刺激的场面,好像她站在三英尺之外的地方,用沙哑的嗓音要求爱抚。但这首琼妮·米切尔[16]的歌似乎更像是声乐老师喜欢推荐的曲目,她唱得很不错。
她唱着流云、爱和生活,这时一个身穿蓝色细条纹西装的时尚小个子男人走了过来,他系着红色的背带,头上涂满发胶。他走到她的身边,站在那儿,满脸不耐烦。他大约三十五岁,长相英俊,派头十足,颇有点迈克尔·道格拉斯的架势,好像《华尔街》里的戈登·盖柯。
我把最后一段重复弹了两遍,他瞪了我一眼,轻轻抬起下唇,以防他交叉的双臂没有传递出足够的信息。等她唱完最后一句,他便往小费罐里丢了一枚硬币。我演奏完整首歌,以为表演到此为止。“戈登·盖柯”走开了,但我的歌手却还留在台上,站在我的旁边。
“你会弹《早上的天使》[17]吗?”她问。
我弹了个A调***,挑了挑眉头,她似乎很满意这个调子。大概是想看看自己能唱多高吧,我猜。作为回应,她清唱了第一句。
我不自觉地开始抬起脚跟,再放下,打起了节拍。如果你只是点点脚尖,节奏感只会停留在你的脚上;如果你抬起脚跟,就能感受到音乐在你的周身流淌。我能感受到的不仅有音乐。她的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轻轻按了按。这是一种无比亲密的举动,特别是当我们的眼前,还有四周,都围着一大群观众的时候。我不在乎是不是有人看着我们——就这样吧,只有我和你,谢谢你陪伴着我,在我身边。
一阵高声的咳嗽传了过来,还有来自同一位看护人的厌恶眼神,仿佛在说:再敢多弹一个音,就把你的胳膊拧断。
我又弹了一个E调。我正身处在墨尔本的一家酒吧,又不是芝加哥南部,那个穿西装的英俊男子也不是莱洛伊·布朗。
他看着我,我的歌手看着我。然后他们互相看着对方,接着他们开始向门口走去。她的脸上还挂着浅浅的黑色印子。
我本就应该让他们走的。他们是酒吧的客人,没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除了那笔少得好像在羞辱人一般的小费。
或许是为了回应他对她的肆意摆布和她的默许,几分钟后,我鼓起勇气在所有的观众面前弹起了一首充满挑衅意味的歌曲。
或许我只是在办公室度过了难熬的一天。我被安上了一个“海鸥”的绰号,因为有一个笑话是这么说的:所谓顾问就像是海鸥,飞进来,胡乱扇扇翅膀,嘎嘎乱叫一通,往每个人身上都拉一摊屎,就飞走了。或许这就是我应得的名号吧,一直给人留下用力过猛的印象,希望能以此让我心安理得地领取普通雇员三倍的工资。在技术上,我已经为项目做好了准备,但在这场咨询的竞技中,我还是嫩了点。
当然,还有小费。戈登·盖柯肯定不知道我还有一份收入颇丰的全职工作。我仿佛变成了我已故的父亲,为他上演了一出列侬—麦卡特尼式的送别表演。
“《你会失去那个女孩》[18]。”
他们两人一同转过身。周围太暗了,我看不清他们的表情。一曲终了,仿佛还在假装只是碰巧选中了这首曲子。场景比我想象的还要古怪。他们停在门口,听我唱完了整首歌,宣告要把她从他的身边夺走,耶。
耶,耶,耶。最终,还是我失去了那个女孩。
嘿,电脑屏幕说。
喵,埃尔维斯说,蹭着我的腿。
妈,电话说,很快便归于沉默。
一次解决一件事。
“我拿到结果了,”妈妈说,“恐怕不是好消息。”
我了解她,所以我不会说出“这个时候去拿结果太晚了”这种不痛不痒的话。时间已经过了晚上十点。
“我几个小时前就拿到结果了,但我不想毁了你的晚餐。”
“噢。”
“他们什么都检测不出来。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问题。”
妈妈没有患上癌症,这种倾泻而出的轻松感立刻引发了她对盲目乐观主义的训诫,同时还有对我童年往事的回顾,尽管我很想忘掉这些事情。
“嘿”还在望着我。这是连接过去的入口,也是对现实的一次检测,但也止步于此。她仍在一万英里开外。小酌一杯也无妨。
我给小猫的水碗填满水,走回到电脑前。克莱尔已经睡下了。
回复发件人。
嘿。我的手指在鼠标上方盘旋着,我又看到了她,站在钢琴旁边,脸上挂着泪痕,拼命掩饰着自己的紧张。她把我当成了她的盟友:“我只是很喜欢你的口音。”
删除。
你好啊,姑娘[19],我敲下这几个字。
发送。
[1]原文为MySentimentalFriend,英国乐队赫尔曼的隐士们于1969年推出的作品。
[2]原文为LikeaPrayer,美国歌手麦当娜于1989年推出的歌曲,亦有同名录音室专辑。
[3]原文为theBonzoDogDoo-DahBand,成军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国乐队,曲风涵盖喜剧摇滚、迷幻流行、前卫流行等。
[4]原文为WalkAwayRenée。
[5]原文为VanMorrion,英国著名歌手、词曲作者、乐器演奏家。
[6]原文为BrownEyedGirl。
[7]原文为BecauetheNight。
[8]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经常提到的点心。据说普鲁斯特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吃到了这种点心,熟悉的味道唤醒了沉睡在心底的所有回忆,他开始回想自己的一生,《追忆似水年华》由此诞生。
[9]原文为PattiSmith,诗人、画家,20世纪70年代美国朋克音乐的先锋人物之一,被誉为“朋克教母”。
[10]原文为EricClapton,英国音乐人、歌手,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吉他手之一。
[11]原文为OliviaNewton-John,澳大利亚流行音乐歌手。
[12]原文为DebbieHarry,美国歌手、演员,金发女郎(Blondie)乐队主唱。
[13]原文为DaydreamBeliever。
[14]原文为DavyJone,出生于英国,歌手、演员,美国门基(theMonkee)乐队主唱。
[15]原文为BothSideNow。
[16]原文为JoniMitchell,加拿大传奇女音乐人、画家、诗人、视觉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
[17]原文为AngeloftheMorning,由美国歌手马瑞琳·拉什(MerrileeRuh)演唱,发行于1968年。
[18]原文为You’reGoingtoLoethatGirl,披头士乐队发表于1965年的一首歌曲。
[19]原文为Ayupla,典型的英国约克郡表述方式。